天还没亮透,老李头就把我从木板床上拽起来。海腥味混着柴火烟钻进鼻子,远处传来浪头拍打礁石的闷响。"后生仔,赶潮水要趁早!"他甩给我一件油光发亮的防水围兜,自己弯腰收拾起船舱里的尼龙网。
第一网银光
舢板在墨蓝色的海面上摇晃,柴油机的突突声惊飞几只早起的海鸥。老李头左手把着舵,右手在裤兜里掏了半天,摸出半包皱巴巴的"大前门"。"看那片泛白的水纹没?"他吐出烟圈,下巴朝东南方点了点,"那里藏着鲳鱼群,游起来像银元宝打转。"
- 凌晨4:23:北斗星还斜挂在天上,我们已经下好二十张流刺网
- 5:47:东边泛起蟹壳青,海平线开始泛金光
- 6:15:收网时拉上来三只透明水母,触须缠着两条拼命甩尾的黄花鱼
渔获里的意外来客
第七张网突然沉得反常。我咬着牙往后拽,网眼里突然闪过一抹翡翠绿——居然是条半米长的鹦哥鱼!它彩鳞上的花纹像是有人用毛笔蘸了靛蓝和藤黄画上去的,尾鳍拍在甲板上发出"啪啪"的脆响。
| 常见渔获 | 罕见渔获 | 危险渔获 |
| 小黄鱼 | 锦绣龙虾 | 蓝环章鱼 |
| 带鱼 | 玳瑁龟 | 狮子鱼 |
| 马鲛鱼 | 鹦鹉螺 | 箱型水母 |
风雨欲来的午后
晌午的日头能把人晒脱皮,我们正往岛西的背阴处躲。老李头忽然抽了抽鼻子,把刚点着的烟摁灭在船帮上。"闻见没?风里有铁锈味。"他说的"铁锈味"其实是低气压带来的臭氧,远处积雨云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堆成黑塔。
暴雨来得比想象中急。浪头把船抛得像个核桃壳,雨水糊得睁不开眼。老李头扯着嗓子吼:"抓紧舵轮!看见那个月牙湾就右满舵!"我眯着眼在雨帘里找参照物,忽然瞥见礁石群中有个模糊的洞口轮廓。
岩洞里的旧时光
躲进山洞才发现别有洞天。潮水褪去的石壁上,留着深浅不一的刻痕——是不同年代的潮位标记。最下面有道歪歪扭扭的"昭和十三年",往上半米有褪色的红漆写着"1963.8.15",最新的刻痕离洞顶只剩两掌宽。
- 石缝里卡着生锈的鱼叉头
- 朽木船板上堆着青花瓷碎片
- 岩层里嵌着半枚"乾隆通宝"
月夜下的赶海人
退大潮的夜晚,整个滩涂变成闪亮的黑镜子。老李头教我认沙面上的气孔:小圆洞是蛏子,八字纹是花蛤,冒泡泡的是月亮贝。月光下,滩涂上到处是佝偻着腰的赶海人,头灯的光点像散落的星星。
| 赶海时段 | 收获 | 危险系数 |
| 朔望大潮 | 青蟹、象拔蚌 | ★★★★ |
| 普通小潮 | 海瓜子、泥螺 | ★★☆ |
| 台风前后 | 冲上岸的深海鱼 | ★★★★★ |
潮水开始回涨时,我的塑料桶已经装了大半。老李头却突然把刚挖到的猫眼螺扔回海里,"带籽的母螺不能抓,这是老辈传的规矩。"他脚边的盐罐子敞着口,说是给来不及回海的贝类续命用。
离岛前的最后收获
在渔村的最后三天,我跟着修补渔网的阿婆学打"水手结"。她布满老茧的手指灵活地穿梭在网眼间,讲起年轻时遇到的怪事:有年冬天捞上个密封玻璃瓶,里面装着日文写的求救信;还有次收网时拖上来半截珊瑚,断面处粘着枚金戒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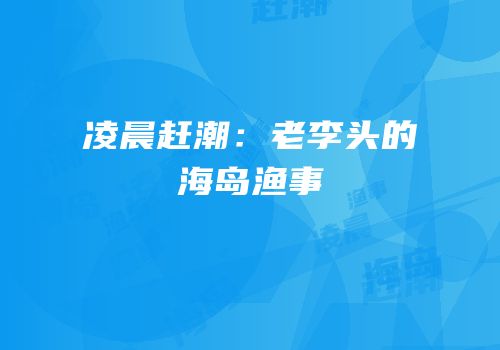
离岛的渡轮鸣笛时,老李头往我怀里塞了个竹篓。掀开芭蕉叶,是晒得半干的墨鱼枣,闻着有阳光和海风的味道。船舷边泛起白沫,远处的渔村渐渐缩成虚线状的剪影,只有那面补丁摞补丁的帆还看得真切。
